Dave:讀《博學者的自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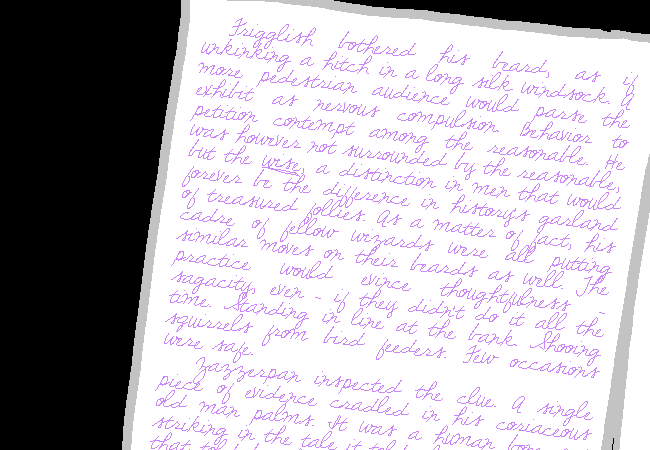
費格理須纏弄著他的鬍鬚,彷彿在解開被作為風向標的細長絲線在飄颯時給繞上的結。若有庸人見得,會將其解析為因神經緊張而不由自主的表現,是在明理之人面前會遭蔑視的行徑。然而在他身旁圍繞的不是明理之人,而是智者,人類中的卓越個體,此族歷史鉻記的愚蠢之冠是永遠無緣置於這種人頭頂上的。事實上,他的巫師隨從們也都在對自己的鬍鬚做類似的動作。此舉應可明示其思想之深刻,或甚至是睿智,如果他們不是無時無刻都在這樣做的話:站在銀行的排隊列中時,把松鼠從鳥飼盆上噓走時。幾乎沒有場所是安全的。
薩哲潘審視線索,他的革質老掌撫抱的一件證物,那是塊人骨,所獨自訴說之言實不如比綴於萬人塚的沼泥上的成千此物吸睛。那塊毛骨悚然的空地給人一種頹爛糕點的風調,一如斯馬尼在節日時做的那塊大得可怕的乳脂鬆糕,它被輪子給晃爛了,令一個小國家舉國哀嘆。
「你肯定?」費格理須問道,儘管他正在弄他的鬍鬚,他的思緒其實正浸淫在意味深長的冥想當中。
「恐怕我會隨你頸上懸掛的艷俗鐘錶咕噥出的一個個可怕的滴答聲而愈加肯定。」這話有所指涉,要知道費格理須帶著一只薩哲潘不合意的錶,那錶有魔法。「希爾斯戈內伏的屠殺並不如所記載的一樣發生。」
「是什麼使你確信這黑暗中的手出自我們的門徒?」依克色庫土司插話道。
「我確信...我...」一張胖臉結結巴巴的念著,眼珠子因著做賊的罪惡與託辭的分崩離析在眶裏疾飛。「我能要求一場...更輾壓的質詢...」不,斯馬尼,現在沒有人會想做要什麼黏黏的邦特麵包的。
薩哲潘的耳朵從而下意識地試想各種質詢的問詞,有些糕點相關的,有些不是。他深邃的身影輪廓在這鋪蓋大地數世紀久的濃霧裡鉤勒出了一幅沉思的形象。他的十一個同儕也一同享受了這令他們偉大的佈道士學者錯愕至啞了的驚訝。少有巫師能答出如此機智的暗語,也少有人能以如此清晰的神志說出。當薩哲潘以肅靜應人時,他鮮少不是受到明慧與理智齊備的話語的還答。
心念著就折騰。博學者薩哲潘為世人稱道的「巫師的自滿」本因其偉大的後繼者而矚目。那些受誠善者奧開特欽點審核過、受豐厚者加斯特里爾試驗過的門徒們,那十二個最甜美、最勤奮好學,長者的雙眼能激起他們的火花的孩子。不該是陰溝裡的、時常遭粗俗的淫穢者利用的浪兒。那些滿口謾罵的小乞丐的心被腐敗,有如掉在地上的香蕉轉褐。中選的年輕人的叛變不僅是令人無法想像的,而是在尊貴不阿議院的高庭裡,向那些軟顱先知的顳骨打去的一陣揮擊。
薩哲潘額上飽受智慧衝擊的眉愈消消減,述說著他對將來之繼承者的眾多教導。那些教導要增進的人類的啟迪與繁榮,卻也正是這場冷酷的追殺欲死命除盡的。這樣使博學者不能休息的於其極昂貴的尖角帽下深奧的歧管路之中研剖至此的謎團甚是罕有,膽敢使他憐愛的眾學子辛勞於汙濁蕪穢之中的,那歷史的惡玩笑--自始迄今的奧祕苦難之源,它用瀆神的魔法建立起一個文明,然後用歡愉的邪淫將它拆毀,逕自地顯明其在智性上的侵襲,使巫師缺鈣的骨頭打顫。
然仍舊更膽敢的是現在這裡唯一重要的問題,一群穿著荒謬外衣長著鬍鬚的散亂老人們能獵捕到他們嗎?他沒有答案。只有個簡單的意見,那麼率直且一反常態地稚氣,對於一個受稱頌的賢者而言,它不證自明之處竟是如此的令人驚豔。
「我們會需要更多的魔杖。」(哇,想點更好的吧。)
Homestuck的著作權屬於Andrew Hussie,這是讀者製作的非官方非營利目的翻譯版本。
詳見
著作權聲明。
 Blogger站 |
官方首頁
Blogger站 |
官方首頁
 Homestuck是什麼
Homestuck是什麼
 頁面清單
頁面清單
 翻譯貢獻人員 |
相關連結
翻譯貢獻人員 |
相關連結